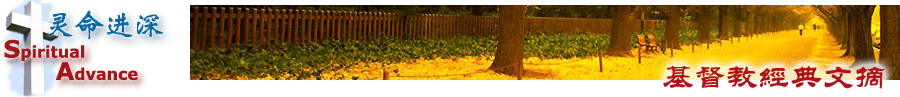
2023年
四月刊 | 一月刊
2022年
十月刊 | 七月刊 | 四月刊 | 一月刊
2021年
十月刊 | 七月刊 | 四月刊 | 一月刊
2020年
十月刊 | 七月刊 | 四月刊 | 一月刊
2019年
十月刊 | 七月刊 | 四月刊 | 一月刊
2018年
十月刊 | 七月刊 | 四月刊 | 一月刊
2017年
十月刊 | 七月刊 |四月刊 | 一月刊
2016年
十月刊 | 七月刊 |四月刊 | 一月刊
2015年
十月刊 | 七月刊 |四月刊 | 一月刊
2014年
十月刊 | 七月刊 | 四月刊 | 一月刊
2013年
十月刊 | 七月刊 | 四月刊 | 一月刊
2012年
十月刊 | 七月刊 | 四月刊 | 一月刊
2011年
十月刊 | 七月刊 | 四月刊 | 一月刊
2010年
十月刊 | 七月刊 | 四月刊 | 一月刊
2009年
十月刊 | 七月刊 | 四月刊 | 一月刊
2008年
十月刊 | 七月刊 | 四月刊 | 一月刊
2007年
十月刊 | 七月刊 | 四月刊 | 一月刊
2006年
十月刊 | 七月刊 | 四月刊 | 一月刊
2005年
十月刊 | 七月刊 | 四月刊 | 一月刊
2004年
十月刊 | 七月刊 | 四月刊 | 一月刊
2003年
十月刊 | 七月刊 | 四月刊 | 一月刊
2002年
十月刊 | 七月刊 | 四月刊 | 一月刊
2001年
十月刊 | 七月刊 | 四月刊 | 一月刊
2000年
十月刊 | 七月刊 | 四月刊 | 一月刊
1999年
十月刊 | 七月刊 | 四月刊 | 一月刊
1998年
十月刊 | 七月刊 | 四月刊 | 一月刊
1997年
十月刊 | 七月刊 | 四月刊 | 一月刊
1996年
十月刊 | 七月刊 | 四月刊 | 一月刊
1995年
十月刊 | 七月刊 | 四月刊 | 一月刊
1994年
十月刊 | 七月刊 | 四月刊 | 一月刊
1993年
十月刊 | 七月刊 | 四月刊 | 一月刊
1992年
十月刊 | 七月刊 | 四月刊 | 一月刊
1991年
九月刊 | 七月刊 | 五月刊
三月刊 | 一月刊
1990年
十一月刊 | 九月刊 | 七月刊
五月刊 | 三月刊 | 一月刊
1989年
十一月刊 | 九月刊 | 七月刊
五月刊 | 三月刊 | 一月刊
1988年
十一月刊 | 九月刊 | 七月刊
|五月刊|三月刊 | 一月刊 |
1987年
十一月刊 | 九月刊 | 七月刊
五月刊
1986年
十一月刊 | 九月刊 | 七月刊
五月刊 | 三月刊 | 一月刊
1985年
十一月刊 | 九月刊 | 七月刊
五月刊 | 三月刊 | 一月刊
1984年
十一月刊 | 九月刊 | 七月刊
五月刊 | 三月刊 | 一月刊
1983年
十二月刊 | 十月刊 | 八月刊
六月刊 | 三月刊 | 一月刊
1982年
十二月刊 | 十一月刊 | 十月刊
九月刊 | 八月刊 | 七月刊 | 六月刊五月刊 | 四月刊 | 三月刊 | 二月刊 | 一月刊
1981年
十二月刊 | 十月刊 | 七月刊 | 四月刊 | 一月刊
至聖所的聖徒-特司諦更
一、出生與少年時代
吉爾哈特.特司諦更(Gerhard Tersteegen 1697-1769)於西元1697年11月25日,出生在德國西發里亞的摩爾鎮。他是一位商人韓瑞.特司諦更八個孩子中的老大。
他在童年時,就已展露出不凡的才華,因此,他的母親就把他送往摩爾的拉丁語學校中就讀。他身體纖弱,良心柔細,勤勉地全力攻讀希臘文和希伯來文。因此,就奠定了以後頗淵博的學識根基。在拉丁文方面,他讀得如此出色,以致有一次在某個公開的慶典中,他以拉丁文發表了一篇詩體的演說詞,而贏得了滿堂的喝采。
他在十五歲時,遽遭父喪,因為母親經濟的情況,他被迫輟學,改送往親戚家中做四年的學徒,這位親戚是魯爾河邊曼漢城的一位商人。
二、悔改與重生
十六歲在曼漢做學徒的這段期間,特司諦更就遇著了神的恩典而大受感動。這是因為認識了一位敬虔的商人,在與他交往中,那年輕的特司諦更心裏,就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。以致他迫切地渴慕要有一個心意的改變,因此,就整整花了好幾個夜晚來禱告、讀經與操練敬虔。接著發生的一個插曲可能促使他在本質上深深地覺醒。
有一次,他被打發到杜易斯堡去;當他在杜易斯堡的森林中時,他忽然被一種劇烈的疼痛所攻擊,覺得快死去一般。他離開路邊一小段距離,迫切地懇求神拯救他脫離這樣的疼痛,延長他的性命,好讓他能夠有更多的時間預備自己來迎見永遠。突然他的禱告蒙了垂聽,痛苦就立刻地消除了。因著這個禱告蒙了應允,這位敬虔的青年人,就深覺必須把自己完全地、毫無保留地獻給這位善良、憐憫的神。
三、靜居、簡單的生活與服事貧窮
特司諦更領悟到屬地、暫時的事物都是全然虛幻,惟有那永遠、屬天的事物在他看來,才是全然地寶貴與偉大。因此,四年學徒期滿,他就選擇了另一項更安靜的職業,因為他發覺一個商人的生活太分他的心了。為著同樣的目的,他一直過著單身的生活(雖然他並不反對婚姻)。
因為,他相信這樣他可以更多地愛他的神,也更好地服事他的鄰舍,超過有妻兒要照顧的情形。因著與一位敬虔的麻布織工認識,他決定去學這門手藝,可是他脆弱的身子,是無法承擔這項工作。因此,他便選擇了織絲帶的職業,(莫以為特司諦更只是一位未受教育的織工,其實他從事這門手藝,只有幾年工夫而已,這不過是一項暫時解決他生活的方法。)他的餘生,都是在魯爾河邊的曼漢度過。
現在,他正是按著他所嚮往的方式生活,安靜而簡單,他的衣著與食物都是很樸素的。食物--多半是親自預備--多半包括麵粉、水和牛奶。
在前幾年的獨居生活中,他每日只吃一餐,也不喝茶或咖啡,大體上是真實地力行著一種最深的禁戒各樣慾望的生活。雖然他織絲帶的收入很微薄,但是他對窮人非常地慷慨。晚上他常去探望病人和窮人,盡他所能地施捨。雖然,特司諦更更知道「一切的物品對我們都是一項幫助,而且,這些物品可以在我們的路上支助我們」;然而,他盡可能地尋求不用物品而活。
四、進入神聖的「安靜」
特司諦更退入隱居的生活,主要是為了安靜。在他裏面有一股勢不可擋地對安靜的渴慕。太少的人對這簡單的兩個字--「安靜」領悟出那是永遠的反應,而這正是被沉默、靜肅的特司諦更所得著的。這「安靜」的意義,為他的生命帶來了聖潔之光,使他的靈發出光耀,且為他的靈裏帶來寶貴的平安。這也成為他的職分,來恢復基督教會對安靜的認識。特司諦更愛外面和裏面的安靜。對他而言,虔敬,本質上就是那些世俗化的人很難持守的安靜。
這位曼漢的聖徒,是這世界上最安靜的人士之一。他認為:基督徒很需要「常常進入他自己裏面那神聖的安靜中」,因為惟有這樣,才能聽見神的聲音。特司諦更賦予了安靜一個特別的意義,因為只有在安靜中,方能成就真誠的祈禱,只有當一個人進入靈中的安靜時,他才會在裏面被神遇見。
「在禱告中,我們必須跟神講話,不論是藉著字句,或是用我們的靈,但是,不僅如此,我們也必須安靜在神的面前,好讓祂也能對我們的靈說一些話。」和西班牙的奧秘派一樣,特司諦更也操練裏面的禱告,藉此他認識靈被吸引親近神,而停留在祂的面光中:「祈禱就是仰望那位無所不在的神,且讓我們被祂看見。」(參歌二14、太六6)特司諦更稱這樣的對話為一個甜美的安靜,而他整個的生活化成了一個禱告,以致他可以坐著或必要跟人講話時,裏面仍繼續不住地禱告。
五、滿足的喜樂(約十五11)
在這樣神同在的安靜裏,特司諦更開始發現一種喜樂,是一般置身於外面各樣變化中,以及不斷有新關係的普通人,所完全不能明白的。這種在裏面可意識到的,神同在的實際,產生了一股大能大力運行在他身上,使他的魂裏滿溢出歡呼的喜悅。自這股最清純喜樂的感覺裏,湧出他的見證:「我無法形容當我獨居時祂是何等地歡悅,我常想這世界上沒有一個王,能活得像我那時候那樣的滿足。」
在滿溢的喜樂中,特司諦更向神感謝,好似他已進入了一間內室,沒有任何一個其他的受造者能進入。他已在他自己裏面經歷到:神可以如此完全地滿足一個人,以致跟人的交往再沒有意義了。特司諦更對於外面的影響愈來愈不動心,他的生命宛如一面沉靜、孤單的湖水,清澈而光滑,反應著天上的榮光。
在各樣的試煉裏,他如孩子般向著神的倚靠一直堅固不動搖,且同時享受著裏面極大的滿足。他寫道某次如何因病臥床,甚或躺在地板上十週之久的情形,那時他住在朋友們的家裏,已付了膳宿費,但是他們連打發一個懶惰的女傭來「給我一杯水」都沒有。「但是,我總覺得應當是如此。」
這簡短的註解是何等要緊,「但是,我總覺得應當是如此。」這顯示了何等無限量的捨棄!特司諦更並不怨嘆他的遭遇,卻總是盡量要與神的旨意聯合,因為他相信:「倘若我們具有了聖徒的性情,我們就會在我們的不幸中喜樂。」這種態度是他人十分不瞭解的。他的親戚們看他是愚拙的,不願跟他有任何來往。在經過了各樣裏面的痛苦之後,更大的亮光臨到他。
後來神喜悅把力量賜給他裏面的人,使他如此體會主耶穌使我們與神和好的恩典,以致他這樣充滿了信心被提升至一個地步,能從自己的經歷裏,帶著極大的權能與恩膏來描寫、述說神我們救主的大愛。 (羅五3、9-11)
六、完全的奉獻
特司諦更一直安靜地隱居了五年,後來就發生了一件事,一定可視為是他在靈性前進的一個里程碑。那是在1724年受難週的禮拜四,特司諦更拾起筆,非沾著墨水,乃是沾滿了他自己的血,以極莊嚴的誠摯,在一張紙上寫下了這些話:
「我的救主與新郎耶穌基督,我把自己奉獻給你,完全而永遠地屬於你。我以全心鄭重地宣佈,棄絕一切撒但所能給我的權益與才幹。就是今天晚上,你--我的新郎淌著血,我的基督,在客西馬尼園裏,藉著你致命的爭戰,你的掙扎,你所流的血汗,把我買贖回來歸給你作你的新婦,解開地獄的捆鎖,向我啟示天父的大愛。從今天晚上起,我的心是你的,我所有的愛在感恩中永遠地歸給你、獻給你!從現在直到永遠,不再是我,乃是你的旨意成全!請在我的裏面施令、治理、掌權!」
這一次在吉爾哈特生命中的奉獻,其重要性,乃是在這同時有口才的恩賜賜給了他,並以後寫出了第一首詩。未經尋求,能力忽然降到他身上,好似突有靈感,有頌歌湧至他的唇邊,且同時有詩蘊生在他裏面,他曾在其他的詩中論到這種情形:「並沒有費多少時間,這些詩意與禱詞竟不經意地忽然臨到我,未加任何的修改與潤飾,它們如何地閃入我的腦際,我就照樣地把它們寫在紙上。」
1725年,他接待了一位與自己持相同信仰的朋友韓瑞.松茂跟他一同開始過一個普通的家庭生活。(他是極勉強地這樣做,因為他天性更喜愛獨居,但是,他仍覺得這是主在那時候的旨意。)
每天清晨六時,他們相聚合唱一首聖詩,早餐中讀一些新約,做過敬虔的祈禱後,就安靜地開始工作。到了上午十一點,便各自分離,有自己一個鐘頭的祈禱。到一點鐘再繼續工作,至晚上六點結束以後,再有一小時的時間用為禱告、與神交通。餘下的時間,特司諦更用為翻譯屬靈的作品,以及完成那些收集在他的書--《神聖福氣》與《靈性花園》--中的詩歌。
七、向外開展及工作的果效
當特斯諦更約三十歲左右,他開始有私人的聚會和屬靈的交通。這是因著一位主內朋友的建議和說服所致。特司諦更從未去追求公開的服事,這一切好像都是神所分配給他的。因為人們愈來愈多地來尋訪他,而他也不認為該收回這樣的服事。「就我而論,倘若我能選擇的話,我一定會過一個截然不同的生活。照我自己的心意,我實在更喜歡保持幾乎全然安靜的生活,把自己隱藏起來,只想到神。但是現在,我必須閱讀、寫作且與眾人交往。」然而,他還是接受了這個責任,他的良心不允許他拒絕這項傳福音的工作。
特司諦更公開的生活,是很不顯眼地開始的,並沒有特別重要的事物與他有關。但是,一段時間之後,特司諦更僅單單地坐在他的小屋裏,卻有愈來愈多的人,聚集來圍繞在他的周圍,飢渴地要聽他智慧的言語。沒有任何的宣傳,聽眾的數目急速增加,以致最後必須打開屋子裏的每一扇門,讓三、四百人摩肩接踵地擠在接鄰的房間裏,渴慕能聽見幾句他的話語。連梯子也擺出來,搭在窗臺上,讓外面的聽眾可攀在階梯上聽。從這一幅熱切屬靈飢渴的光景,令人不得不想起使徒行傳中的描寫,這番光景,令人憶起起初基督徒的情形。
八、認識「神的同在」
神的同在,是特司諦更一切努力的起點與標竿。他無論在寫信或是與人交談中,都一直地浸沐於神奇妙的同在裏,這是他在那段隱居的生涯中,所初次經歷到的,且一直地成為他一生生活中心的根基。
在他的生命裏,神的同在就如同車輪的軸心一般,一切的言論均源集於此;且引領他的生活達到一種特別安寧的光景,其中再無恐懼的空處。也就是從這無法形容的神的同在中,湧流出了他傳道的能力,以及灌注了他醫治人魂的恩典。就是單單這個,使我們能認識,為何有那麼大的奧秘影響力,自他裏面發出。這神聖的同在,是他生存不可侵犯的中心--無法形容,然而,他為別人的禱告,仍是:「凡口渴的都應當來!白白暢飲得飽足……。」(啟二十二17)
彼亭之隱密處
受牽引進入曠野, 與神單獨同住,
靈與靈在此響應; 心與心相傾吐。
荒渺無人煙彼岸, 我尋得神隱密處;
獨自穿越黃金門, 心愛事盡都棄絕。
除神與我外無他, 哦!遠離世間人!
然縱身塵寰喧囂, 主!仍單獨與你親。
或田野、商市、街道, 仍被你緊緊擁抱,
在彼完全之安息, 甘甜關鎖中無擾。
哦!上主廣大無比, 遠超夢想、傳聞,
千言萬語難述盡, 思緒弗能繪明。
神!自有永有之神! 惟人因與你同行。
心中狂喜如火焚, 方得真識你尊名。
安恬於奇妙同在, 深情懷中靜沉,
面對面仰瞻聖顏, 思慕之年償盡。
除你所賜別無求, 異象奇景亦不羨,
寶血既將天開啟, 我等與你親相見。
困乏者!就近祂 ! 向君所陳一二;
汪洋海中之涓滴, 泉源水淺嘗爾;
因祂親吻聖印記, 我唇已封魂肅穆,
凡口渴者都來吧! 白白暢飲得飽足。
雖然特司諦更在他公開的事奉中,有好幾道路線,但是主要地,他只集中在一件事上。他所有的呼召,只有一個呼召,那就是一個連續不斷地,在裏面親近主的生活。「整個的世界都可以在我們裏面得著:在我們裏面的最深處,有邪惡的奧秘,也有敬虔的奧秘。有撒但的淵藪,也有藉著聖靈而啟示的神性的奧秘……。」這種獨一內在的方向,使得特司諦更具有了世上罕見的靈性,有如來自另一個世界的音樂一般,緊扣人心弦。
以下這番美麗的話語中,可顯而易見:「真實地內在的靈性,是神的傑作,而非出自人手……一個屬靈的魂,即使在他什麼都沒有做的時候,已經做得足夠了。一種安靜的安息、一個安靜的默許、一個簡單的守望,這些,就一個讓神作工的靈都已足夠了。」我們摸著特司諦更裏面的人,正是他生命裏最真實的部分。
特司諦更最盡心竭力所做的,乃是引導裏面的人進入安息裏,好使他能領悟神的同在。更進一步,他擁有了那奇妙的恩賜,就是向人揭示那無法測度的神同在的重要性。他指出,那是比僅僅在頭腦裏對於神性的觀念,還要超越出不知多少呢!
特司諦更最深的努力是獻上:進入神的同在。不必說什麼,或做什麼--只要住在祂裏面。他努力要得著這個,而且只要得著這個。這對他就足夠了,正如他在一首詩歌中所描寫的那樣實際地,揭啟了他生命旋律中所滿溢的那和諧的主題曲調:
神是無所不在:讓我們來敬拜!
拜祂就於此地,神在我們當中。
裏面全然肅穆,一切向祂俯伏!
凡真認識祂者,凡真認識祂者,
闔上你的雙目,來吧!再向祂降服。
神的同在,是特司諦更一切努力的起點與目標!無論他做什麼,他總是在神這奇妙的同在裏。並且從神的同在中,流溢出他講道的能力,以及所賜給他的那醫治魂的恩典。惟有這點能夠解釋他所傾倒出來的那股奧秘的影響力。那神聖的同在,是他生存所不可侵犯的中心。它無法形容,卻是特司諦更生活的奧秘,也是他被尊為聖人的原因。
九、特司諦更由親身的經歷中對神和基督耶穌的認識
對於聖經,特司諦更自主領受了何等的亮光,與何等深邃的洞察力阿!從他一切的寫作裏,可以顯示出來,尤其是他的某些講章,讓讀者不只是停留於外面人的智慧上,乃是直接地被引向裏面的中心。同樣地,從他的作品中發出一股亮光,顯示他親身地認識神和祂的法則。
在1738年,特司諦更病危了,似乎沒有復原的希望,他用以下的話語來跟他的朋友道別:「我在神裏面,有極大的平安,還有這些我所要留給你的著作。我所寫的一切,我已經都親自地經歷了,這是何等重要的真理,因此,我可滿足地步向永遠了。」
他向另外一位朋友寫說:「我是這樣走入永遠,一個貧窮、卑微、不配的人,只能盼望且更超乎平常的全心倚靠神,因著祂的憐憫接納我。同時,我感謝我的主,祂允許我能活得這麼長,使我已經真實且從裏面認識了祂。除了我的軟弱以外,我不能不把這一切都歸因於神浩大的恩典。哦!多麼美好能單單地知道神是那位獨一的、自有永有的!真的,認識神就是永生!人總是渴望多知道什麼,甚至對屬靈的事,也是這樣,這是充分的證明他們,還沒有真正地認識神。神對於各方面都是足夠了;單單祂的自己就足可以且永遠地祝福、滿足我們那無法想像地大容量的智慧的眼睛。」
神和祂裏面的一切,祂一切的作為和法則,是受造者的靈裏真實的食糧與祝福。我們所有的好處都在祂裏面。只要一想到--神就是一切,祂是最偉大的、憐憫而賜福的神--我就得著異常的滋潤。
嬰孩的道路
「神的法則,是何等的奇妙、何等地難測阿!它總是跟我們所想的不一樣,……那是一個不斷失去的道路,直到一個人成為如此地貧窮,以致再沒有什麼可失去了。--現在,只要一直奉神的名,往前!讓祂掌權!單單地讓祂來活;人只要像一個搖籃中的嬰孩般,天真地仰望就好了!人只需在心中如此地認定、如此深的敬拜、如此出自肺腑地說:『主是何等的良善,配得我們的愛戴!主所作的一切,無不良善且誠實。』
「當我想到神已為我們選擇了一條救恩之路,我就不能不敬拜,且失去自己在祂裏面。這條救恩之路,乃是祂從受造者的身上取去一切,把它們都歸神的道路。這結果使我們很快樂地、需要更親密地依附著祂,住在祂裏面,裏外都活在祂裏面,成為在靈裏一直都是貧窮的,好使一個人能真正地擁有一切!這是一條為著嬰孩的道路,是為著那已經從每一件事上,都倒空他們自己的嬰孩而預備的,聰明人不認識這條路。只要人渴望擁有或抓住什麼,這條路就是窄的。那遠遠地尋找這條路的人會錯過它,但是,那跟隨基督所拋給我們慈繩愛索的人,會發現它近在咫尺。
「神對我們而言必須成為一位實在、真實而賜福的神,因為我知道:凡已經親身且有一點經歷,並認識祂的人,必會愛祂且讚美祂,因為祂是配得的。即使祂也許引領他們經過枯乾、黑暗的道路。我有一點得知這些,使我能夠說:在我們裏面,只有軟弱和邪惡罷了!(真正相信這件事的人,多麼的少阿!)在主耶穌的裏面,卻湧流出一切--一切我們所需要的!
「直到如今主都一直地幫助著我,祂直到如今的幫助激勵我相信,祂必幫助我到底。
「常令我感到難過的是:如此的一位神--這樣在裏面向我們顯現,這樣完全滿足我們的那位良善的主--竟是這麼少人追求、認識與愛慕祂 !」
向著一切他所接觸的人,特司諦更為他們指出:單單要主耶穌,只有主耶穌;並頌讚祂,只為著一個原因:祂是我們的拯救與救贖。向著一位快要分別的友人,他呼出:「主耶穌的救贖、主耶穌的話語、主耶穌的靈、主耶穌的模型!」對著另一位批評他思想太過簡單的人,他在其他的事中回覆他說:「那將是我極大的安慰,倘若我能在離世前的一?那,就在那即將到神面前、我的最後一刻,能向著一切受造的呼喊說:單單神的自己是生命的泉源,再沒有其他的道路能夠得著、並享受這位神,除了藉著那由基督的死所打開的,又小又窄的道路--就是裏面的祈禱、與基督同死,一同藏在神裏面的『內在生活』之路。」
十、特司諦更的信心
「我的神學思想和信心是這樣的:」特司諦更對一位想要拉他加入另一個團體的人,如此說:「我,正如一位藉著基督的寶血,得以與神和好的人。可以每天藉著死、受苦和祈禱,藉著耶穌的靈,讓我能被引導棄絕自己,棄絕一切外面的事物和各樣關係,藉著耶穌基督得以完全地單獨住在神裏面。好使我因著信與愛,緊緊地抓住這位我自己的神,相信藉著聖靈和藉著祂在基督裏無瑕的憐憫,能夠與祂聯合,達到那永遠的救贖。向所有的人,無論他是那一國,只要是擁有這個目的的,我就與他有著相同的信心,我因他們是神的兒女而愛他們,跟那些在我自己的團體中,與我緊緊聯合的人,是一樣地由衷地出於裏面的愛。」
當被問及那些來到他那裏的各樣人的信仰如何時,特司諦更回答說:「我不問他們是從哪裏來,我只問他們要往哪裏去。」
(一)「與神同在」的生活
特司諦更對神深切的認識,一直繼續地影響他的感覺和心思。他的心完全被神的同在所充滿、所吸引。他所有的舉止和生活的態度,所呈現給人的印象,是他裏面對神的敬畏與對神的愛,而這位神是時時在他的裏面顯現。他滿有確據地相信:神非常特別地顯現在他的裏面。他一直是這樣地想著:神正摸著我裏面的人。所以祂就時時地把他裏面的人,在這位無所不見的神眼前,很誠實地敞開,好使他能被神照亮、溫暖而甦醒。他一直操練著單單地仰望神。對別人,他必讚揚神在一個魂裏的顯現,真是一項特別的恩典。並且提醒他們:不是藉著我們自己的努力和力量,乃是藉著這可愛、甘甜、大能而甦醒人的同在,使新生命得以被喚起,且保持在我們裏面。從他的著作《珍珠》的序文內,把神同在的三方面給予了最佳的解釋:
(一)神無所不在的同在。
(二)神藉著恩典的顯示的同在。
(三)神內住所顯示的同在。
從他的另一本著作《真理之路》裏,我們可以找著關於操練與神同在,和一個人應當如何地尋求神與祂的面(同在)的最佳教導。他的論述中,我們可以看見:那是出於極其的虔誠,以及自己的經歷而寫出。在他的一封信裏,他寫說:「惟有主耶穌的靈,才能給我們真實的美德。祂在我們裏面如此地親近--純淨地注入賜生命的能力,就能夠治死老我、治死天然的成分,使得一個人能夠存心忍耐地前奔,(來十二1)並且毫無怠惰地靜坐。(約十一28-29)因為主耶穌成了我們的意志、我們的生命和我們的心志。因此,那行走在這條裏面之路上,進入了裏面人中的安靜,不住地禱告,一直地等候著神,把他們自己交予這位獨一賜生命之神的人,是何等地快樂阿!」
(二)「與神同在」的事奉
「當我完成一個工作,舒服地坐著時,我就想:一旦我們到達那裏的時候,將會如何?所以,當我們在服事這位良善而信實的牧人時,不要困倦、沮喪,因為就在服事祂的時候,為人類帶來了極多的祝福。我們的力量,真是非常微薄、渺小而脆弱,但是我們不要考慮這些,也不要把我們對祂的服事,看為一種職責而已,乃要看它是一項喜樂與祝福。……我們豈不是應當現在就好好地做它,而非等候我們能做得很完全的時候,才去做?不然,我們就必須等太長的時間了。讓我們繼續地往前吧!即使需要在?弱中來做。只要在禱告、受苦、否認自己與忠信中,……繼續下去,即使仍會有許多不應當有的事發生,或偷偷地滲入,仍要如此。每個人必須認識他自己的錯誤,謙卑自己,然後持續地往前,……我只願所有的人,即使是剛剛開始與神同行的人,要以正確的眼光,來看他們對神的服事,看它為喜樂與祝福。」
交託神並討神的喜悅
「我們不應當自己去做什麼,或渴望去抓住什麼,只要把我們自己和每一件事都交在神的手中。聖善是屬祂的。祂可以隨祂自己所喜悅的賞賜或支取。當我們得著那些聖善的事物時,它們對我都顯得不怎麼聖善,然而,最令我無限高興的是,單單主自己是聖善的!……惟獨在主的裏面,才是我們的救恩。祂自己是我們的拯救,是我們完全的榮耀。……祂對祂所創造的人的要求,就是--照祂所是的,把自己交託在祂的手中,以後,就很少再想到他自己,如同他丟棄一樣東西後,就很少再想到它一般。……在祂的手裏還會有任何需要麼?祂對我們的照顧會不夠麼?
「凡在我裏面的都被吸引(傾慕)於獨處、安靜(無形、無以名狀)、與神聯合、與神同在。哦!這才是生活,能這樣地度日,這對我而言,是我小小的天地,我的滋養(筵席),我天職的目標:從所有的一切被倒空、分別出來,單獨地在靈裏與神同活。讓屬己的一切都靜寂,讓神和屬神的一切得著地位--這是真理、力量、生命與祝福的惟一出路。哦!為我所餘留的這短暫時光,是何等地寶貴阿!我好像一直受到攔阻,使我不能愜意地享受這樣的生活。但是,無論在時間中(現在在地上),或在永遠裏,我惟一所渴望的,只有討神的喜悅,完全為神、愛神;我寧願在一切的攪擾、痛苦和難處中這樣生活,也不願為自己活而享受萬有和許多的安逸、舒適……。
「在這地上,除了保羅的要求(林後五9--所以無論是住在身內,離開身外,我們立了志向,要討主的喜悅)以外,我不知道我還有什麼其他的要求。雖然並非完全地跟保羅一樣,我乃是:無論在家,或是出外旅行,都要討神的喜悅。自愛只會想:我除了能在天上外,還能擁有些什麼?卻不願為它付更大的代價;但是,在敬虔之愛的眼目中,天上不是這樣。單單討神喜悅才是天上,才是尊貴和榮耀!」
十一、末了的話
除了一段受試探的時間以外,吉爾哈特.特司諦更對神的自己,總是堅信不移。既然他已經充滿了這樣的信心:神,毫無疑問地,已顯現在他的裏面,因此對他來說,再不會有什麼嚴重的問題了。起先聽起來這也許有點簡單,但是,正如每一件簡單的事一樣,它是最重要的事,並且是一件令人只能以戰兢而喜樂的心來說的事。這種對神在基督徒的裏面不間斷同在的信心,就是特司諦更信心最中心的地方,自其中發出那顯然可見的能力。
「這種對神滿有憐憫、裏面而甘甜的同在的信心,是最有能力的方法,使魂得以快速地達到成聖。」
「神在我們的裏面,是在比我們自己最裏面的部分,還要更深的地方,在那裏,祂呼召我們;在那裏,祂等候我們;在那裏,祂與我們相交,使我們沉浸於滿溢的福分中。更甚者,這個同在,我們無法以頭腦來明白它,而是要相信它……。」
這一段高貴的陳述,確實是特司諦更所關心的事物,而不只是道理而已。在古老的傳記裏還多加上一段:「神的同在是如此經常地向他顯現,那樣深刻地銘印他裏面,以致連他所有的舉止和行動裏都注入了一種摯愛的尊敬。他全然把握地相信:神,以祂特別的方式,顯現在他的裏面。他知道神真的在他的裏面看他。」
這有福的神的同在,只能被堅立在那些竭力、不間斷追求的人裏面。有一點必須要強調的是:它與所有其他的感覺不同。它乃是神的自己親自降臨在人的裏面。特司諦更把神的同在,分作三方面:
第一點,祂充滿萬有、無所不在的同在。
第二點,祂恩典的同在,敲響人的靈,提醒他要悔改,或是在一個人日常生活裏的引導和帶領。
第三點:神居住在一個人裏面的同在,這是前二者的結果。
對特司諦更來說,最後一種的同在,是清楚可見的。因為他把全部的生命都獻於追求神、敬拜神、讚美神和愛神了。這是他對神的真實,不可搖動的認識。當特司諦更奧秘地傳講、論到神同在的性質時,是那樣地帶著滿具壓倒性的能力。特司諦更的安靜,使我們面對面遇見了永遠的奧秘,帶我們戰兢恐懼地踏上一地,是一處必須脫去鞋子之地,因這是聖地。神不住地同在,就是特司諦更生活的奧秘,也是他被稱為聖徒的原因。
正如所有的聖徒一樣,特司諦更有一個最實用的態度,來面對死亡。有一次,他寫說:「當一位虔誠人去世時,我們不應當說『他死了』,我們應當說:『他已經去天上;這是他開始天上旅程的日子。』」
這顯示出特司諦更的基督信仰,只是身為一名屬靈的天路客,他對地上的生活,僅有一點點些微的聯合而已。他認為,基督徒不是為這個地而創造的,他不必像一隻地鼠在這地上掘一個洞。他只被認為是一名天路客而已。
來阿!孩子們!我們出發吧!
黃昏將近,停留太危急。
身在曠野,來吧!堅固你心,
直趨永遠,力上加力,
終點何其美麗。
1769年4月3日,淩晨兩點鐘,吉爾哈特.特司諦更呼出了他在這地上的最後一口氣,進入了祂永遠的同在裏,就是他在這地上曾如此地相信,且如此深地敬愛的那一位的同在裏。很可惜,在後代中沒有留下一張特司諦更的畫像,因為他從不允許讓畫筆把他必朽的面目,描繪成不老的容貌。